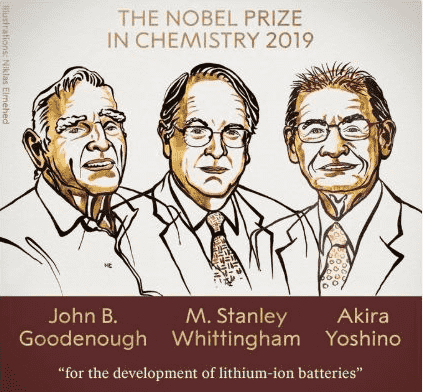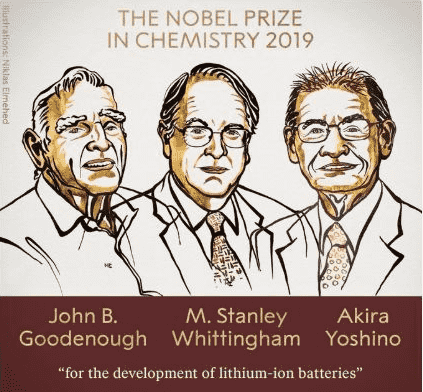16岁那年,我从山旮旯里的初中考入几十里外小镇压上的一所高中,小镇虽然也很穷,但相对于以前那巴掌大的一片狭小天地要热闹得多。 对泥巴里滚大的农村娃来说,我无异于进了繁华的都市。 爹妈一步十叮咛,挑着简单的行李送了我一程又一程。 我换上了赶集才穿的惟一一件土黄色的卡其布上衣,在崎岖的山路上走得如沐春风。 从未出过远门的我,想像着即将到达的那个精彩的“外面的世界”,心里异常兴奋。
可从报名开始,我便陷入了莫名的尴尬。 在财务处排队交学费,当我掏出一大把皱巴巴、汗津津的毛票零币时,竟引来前后同学的哄笑。 “瞧,那个乡巴佬!”“活活脱脱一个陈奂生!”“哈哈哈……”肆无忌惮的嬉笑让我感到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发烫。 这时,我下意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同学:夹克、牛仔、长裙、皮鞋……这些如今在任何一个小乡村都不稀罕的服装,对当时的我都是气派非凡的名牌。 再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束,一双解放鞋裹满泥泞,一条月白色的长裤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,她蹩脚的手艺在被腿上留下了怎么也拉不平的皱褶。 再看看那件我引以为自豪的卡其布上衣,因为浸透了汗水,又粘上了行李袋上的灰尘,脏不啦唧的像只破麻袋套在身上。 入学第一天,我流下了尊严被伤害的泪水。
如果我懂得用汲取知识来填补生活的寒碜,也许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,考上一所理想的重点大学,也就没有后来那段耻辱的历史。 但疯长的虚荣心荒芜了我的理智,我发誓要生活得“体面”一些。
我开始找种.种理由向家里要钱,然后迅速买了一套时髦的衣服,将那套让我底子掉尽的家当毫不犹豫地扔到了垃圾堆。 为了显示我的阔绰和大方,我学会了抽烟、喝酒、玩电子游戏,频频请同学上街“撮”一顿,一点也不心疼地拿父母的血汗钱潇洒。
我的慷慨和义气使我很快结识了镇上的一帮小混混。 我们集体逃课,成天在街上录像厅、台球室打发时光。 功课自然一落千丈,直到上高三最后一个学期,我的大名还稳稳地占据着排行榜上最后一名的位置。 父母问我成绩,我总是东骗西骗满天过海,要么就根本不回家。 除了要钱,我从未给家里正儿八经地写过一封信。 我痛快淋漓地挥霍着宝贵的复习时间,虽偶尔良心发现,但自感浪子回头已晚,继续破罐子破摔,透支着青春。
成天玩乐使我的钱根本不够花,债台高筑的我为了躲避同学的追讨,常常在一帮狐朋狗友家里几天都不进校门。 但没有钱一切的交情就像小河断流一样迅速干涸,污浊的泥沙全部暴露无遗。 最铁的哥们儿也开始对我厌烦了,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将我拒之门外。 虚伪的友谊终于纤毫毕现,我终于醒悟了,但为时过晚。
高考迫在眉睫,但对我来说无关紧要。 我已做好了拿到毕业证就去打工的准备。 但借人家的钱最终还得还,我不想让一贫如洗的家庭再为我背上沉重的负担。 颓唐绝望的我决定孤注一掷,铤而走险。
在我偷卖掉学校的一台电动机后的一周,校保卫处找上了我。 多方调查取得的确凿证据让我无法抵赖,小偷的罪名戴在了我的头上。 除名,罚款,扣发毕业证。 严厉的处罚顺理成章地下来了。 更让我伤心欲绝的是,学校勒令父母必须亲自到学校党委办公室签名接受处理。
那天父亲冒雨走了四十多公里的山路赶到学校,得知事情的原委后,一张布满沧桑的老脸凄惨灰暗,那欲哭无泪的眼神让我不寒而栗。 我想到了一句话:哀莫大于心死。 父亲既没有打我也没骂我,那黯然叹息却像一把刀,割得我的心鲜血汩汩。 那一刻我没有去想怎么走今后长长的道路,而是想到把脸面看得比命还珍贵的父亲该如何活下去。
在接连抽了两包纸烟后,父亲狠狠地抓住我的手,一声不吭地走向校长办公室。 没有多余地交谈,父亲见了校长,就扑通一声两膝着地跑在了地上,“都是我作父亲的无能,我作孽啊!你们怎么处理都可以,我没啥好说的……”稍顿,父亲又苦苦地哀求:“罚多少钱都行,只是求您把毕业证发给他吧!他还十八岁不到,让他到外头谋个活干吧!”我清楚记得,面对四十岁的校长,五十多岁的父亲用不规则的发音将那个“您”字念得非常清晰。 我后来才知道,父亲一门心思地还想让我拿了毕业证到其他学校补习。 父亲恨死了我,可始终不甘心我就这样走出教室。 从小学到初中,我一直是父亲心中的骄傲啊!
可我知道那只是父亲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,早已堕落沉沦的我不想再去面对学校这个圣洁的地方。 我也不敢再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庄。 那里的手指会戳断我的脊梁,唾沫足以把我淹没得不见踪影。 我揣着父亲用人格和血汗钱换来的毕业证,一个人悄悄乘车来到省城。 我的身上只有二十几块钱,苦撑苦挣到第五天我还在一家家工地上徘徊。 从没从事过体力劳动、白净瘦弱的我,想到找一份能糊口的苦力都没门。 不值钱的泪水洗净了我三年的噩梦,也让我彻悟:我不光在本该耕耘的季节错过了播种,我是把整个春天都弄丢了。 我拖着饿得发昏的身子在街上毫无目的地遛达。 华灯初上,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,我看到衣着鲜艳的城里学生骑车飞出校门,他们轻快的的笑声在我身旁一阵风似的飘远了,不像那个曾经属于我的春天一去不复返。 瑟瑟秋风中,我蜷缩在菜市场的一角,静静地停止了毫无目的的游荡。 饥饿和困顿使我发起了高烧,头痛得迷迷糊糊。 黑暗中,我想到了死……
第二天醒来时,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。 我吃惊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空间。 这是一间看起来像储藏室的房子,角落里堆满了各种蔬菜。 床是几块木板搭在两张登子上铺成的,破絮下面露出乌黑的板纹。 离床不远放着一只煤炉,炉上的砂锅正冒着热气。 见我醒来,一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冲我一笑:“终于醒来了?”说着端着一碗稀饭一瘸一拐地走到我的床头:“先喝点稀饭润润肠子,看你一定饿坏了。 ”饥肠辘辘的我也不多想什么,端起碗稀里哗啦喝了三大碗,才算有了点活气。 “谢谢你!”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,想到这几天的遭遇,忍不住痛哭失声。 断断续续听完我的原委,小伙子默默地望着我,叹了一口气:“那你打算怎么办呢?”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“其实,我们不该为一次错误放弃未走完的路。 与其在歧路上越滑越远,不如返回重新开始。 ”小伙子语气很沉重,我则听出几分惊奇:“我们?难道你也有过我现在这样的经历?”小伙子皱着眉点了一下头。
“我那荒.唐而惨重的错误和你很相似。 而且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我的一条腿残了,是和别人打架时伤的。 ”我才想起,他是一个跛子。 “那次斗殴的结果的是,家里被前来报复的人捣了个稀巴烂,母亲气得跳了河。 是我害了母亲。 父亲拿了把刀说要砍死我这个逆子,我就跑了,再也没回去。 父母把我养这么大,不但没有得到我的报答,反而受尽了磨难和伤痛,我有时觉得我真是个十恶不赫的罪犯。 ”他说着说着将双手插进浓密的头发里,使劲地揪扯着,喉咙里挤出嗷嗷的哭声。 我不得不惊奇世事的巧合,一股同病相怜的冲动让我紧紧地搂住了他。
从此,我跟着他一起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干上了贩菜的行当。 我们早上四点就起床蹬着三轮车到郊区,从菜农手里进来一车蔬菜,然后拉到菜市场销售。 我们舍得花力气,菜价比别人定的低,一天下来薄利多销竟能赚得100多元钱,尽管很累,可毕竟有吃有住还能存下一笔积蓄,我很庆幸也很知足。 到了月底,他便将纯收入盘点平分,我坚持不要那么多,却抵挡不住他的强硬:“过去的事都过去了,我们现在是萍水相逢的朋友,能够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,就说明我们找回了自己。 我们并不是不可救药。 ”我就不再推辞。 除掉房租水电费,我们各自赚了800元钱。 他只从一沓钱票里抽出一张百元币,就将钱全部汇到了家里。 “我已三年没回家了,除了给家里汇款,我什么也没让家里知道。 ”他说这话时有点丧魂落魄,黯然神伤。 我也不由想到了父亲。 真不知他们急成了什么样了。 那一晚我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。
我想到了那梦魇般的生活。 人想到了渺茫而又无法逃避的前程。 我想到了父母忍受的耻辱。 难道真的一失足就得悔恨到坟墓吗?难道美好的青春就这样在市井的蝇营狗苟中得过且过吗?我在痛苦中反省自己,我在懊悔中诘问自己。 两个月后,我谢绝了他的挽留,毅然选择了回家重新开始。
刚好家乡在进行征兵体检。 我毫不犹豫地加入应征的行列。 感谢上苍,在历经失落和磨难之后,让我获得了一次涅盘的机会。 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。 如果说一身落时的衣着不可思议的让我迷失了自己,那么一身绿军服则让我奇迹般地获得了新生。 春天离我那样遥远,但我已脚步坚定地上路。
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,站岗放哨,摸爬滚打。 火热的军营生活一点一点融炼着我,敲打着我。 走过青春迷失的幽长隧道,我对黑暗之后的光明更懂得去珍惜和热爱。 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我利用空余时间悄悄捡起久违的高中课本。 第三年,我顺利考上了军校。
如今,军校毕业一年的我,已是一名年轻的共和国军官。 当我威武地走到队列前头的时候,又有谁知道我曾是一名被时光抛弃过的少年呢?站在阳光明媚的军营,我常想,堕落也许只是一瞬间的差错,而崛起则需要一段漫长的挣扎。 只有超越无法回避的过去,你才能获得生机勃勃的春天。 正视那些因为无知而留在履历上的斑点,正视划过心灵天空的阴影,让那段不光彩的灰色经历,成为一根插进神经的芒刺,成为知耻而后勇的不竭动力,这远比忘记它,或逃避它要好得多,因为忘记过去,就意味着否定现在,背叛将来。 作者:阿绍
可从报名开始,我便陷入了莫名的尴尬。 在财务处排队交学费,当我掏出一大把皱巴巴、汗津津的毛票零币时,竟引来前后同学的哄笑。 “瞧,那个乡巴佬!”“活活脱脱一个陈奂生!”“哈哈哈……”肆无忌惮的嬉笑让我感到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发烫。 这时,我下意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同学:夹克、牛仔、长裙、皮鞋……这些如今在任何一个小乡村都不稀罕的服装,对当时的我都是气派非凡的名牌。 再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束,一双解放鞋裹满泥泞,一条月白色的长裤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,她蹩脚的手艺在被腿上留下了怎么也拉不平的皱褶。 再看看那件我引以为自豪的卡其布上衣,因为浸透了汗水,又粘上了行李袋上的灰尘,脏不啦唧的像只破麻袋套在身上。 入学第一天,我流下了尊严被伤害的泪水。
如果我懂得用汲取知识来填补生活的寒碜,也许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,考上一所理想的重点大学,也就没有后来那段耻辱的历史。 但疯长的虚荣心荒芜了我的理智,我发誓要生活得“体面”一些。
我开始找种.种理由向家里要钱,然后迅速买了一套时髦的衣服,将那套让我底子掉尽的家当毫不犹豫地扔到了垃圾堆。 为了显示我的阔绰和大方,我学会了抽烟、喝酒、玩电子游戏,频频请同学上街“撮”一顿,一点也不心疼地拿父母的血汗钱潇洒。
我的慷慨和义气使我很快结识了镇上的一帮小混混。 我们集体逃课,成天在街上录像厅、台球室打发时光。 功课自然一落千丈,直到上高三最后一个学期,我的大名还稳稳地占据着排行榜上最后一名的位置。 父母问我成绩,我总是东骗西骗满天过海,要么就根本不回家。 除了要钱,我从未给家里正儿八经地写过一封信。 我痛快淋漓地挥霍着宝贵的复习时间,虽偶尔良心发现,但自感浪子回头已晚,继续破罐子破摔,透支着青春。
成天玩乐使我的钱根本不够花,债台高筑的我为了躲避同学的追讨,常常在一帮狐朋狗友家里几天都不进校门。 但没有钱一切的交情就像小河断流一样迅速干涸,污浊的泥沙全部暴露无遗。 最铁的哥们儿也开始对我厌烦了,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将我拒之门外。 虚伪的友谊终于纤毫毕现,我终于醒悟了,但为时过晚。
高考迫在眉睫,但对我来说无关紧要。 我已做好了拿到毕业证就去打工的准备。 但借人家的钱最终还得还,我不想让一贫如洗的家庭再为我背上沉重的负担。 颓唐绝望的我决定孤注一掷,铤而走险。
在我偷卖掉学校的一台电动机后的一周,校保卫处找上了我。 多方调查取得的确凿证据让我无法抵赖,小偷的罪名戴在了我的头上。 除名,罚款,扣发毕业证。 严厉的处罚顺理成章地下来了。 更让我伤心欲绝的是,学校勒令父母必须亲自到学校党委办公室签名接受处理。
那天父亲冒雨走了四十多公里的山路赶到学校,得知事情的原委后,一张布满沧桑的老脸凄惨灰暗,那欲哭无泪的眼神让我不寒而栗。 我想到了一句话:哀莫大于心死。 父亲既没有打我也没骂我,那黯然叹息却像一把刀,割得我的心鲜血汩汩。 那一刻我没有去想怎么走今后长长的道路,而是想到把脸面看得比命还珍贵的父亲该如何活下去。
在接连抽了两包纸烟后,父亲狠狠地抓住我的手,一声不吭地走向校长办公室。 没有多余地交谈,父亲见了校长,就扑通一声两膝着地跑在了地上,“都是我作父亲的无能,我作孽啊!你们怎么处理都可以,我没啥好说的……”稍顿,父亲又苦苦地哀求:“罚多少钱都行,只是求您把毕业证发给他吧!他还十八岁不到,让他到外头谋个活干吧!”我清楚记得,面对四十岁的校长,五十多岁的父亲用不规则的发音将那个“您”字念得非常清晰。 我后来才知道,父亲一门心思地还想让我拿了毕业证到其他学校补习。 父亲恨死了我,可始终不甘心我就这样走出教室。 从小学到初中,我一直是父亲心中的骄傲啊!
可我知道那只是父亲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,早已堕落沉沦的我不想再去面对学校这个圣洁的地方。 我也不敢再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庄。 那里的手指会戳断我的脊梁,唾沫足以把我淹没得不见踪影。 我揣着父亲用人格和血汗钱换来的毕业证,一个人悄悄乘车来到省城。 我的身上只有二十几块钱,苦撑苦挣到第五天我还在一家家工地上徘徊。 从没从事过体力劳动、白净瘦弱的我,想到找一份能糊口的苦力都没门。 不值钱的泪水洗净了我三年的噩梦,也让我彻悟:我不光在本该耕耘的季节错过了播种,我是把整个春天都弄丢了。 我拖着饿得发昏的身子在街上毫无目的地遛达。 华灯初上,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,我看到衣着鲜艳的城里学生骑车飞出校门,他们轻快的的笑声在我身旁一阵风似的飘远了,不像那个曾经属于我的春天一去不复返。 瑟瑟秋风中,我蜷缩在菜市场的一角,静静地停止了毫无目的的游荡。 饥饿和困顿使我发起了高烧,头痛得迷迷糊糊。 黑暗中,我想到了死……
第二天醒来时,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。 我吃惊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空间。 这是一间看起来像储藏室的房子,角落里堆满了各种蔬菜。 床是几块木板搭在两张登子上铺成的,破絮下面露出乌黑的板纹。 离床不远放着一只煤炉,炉上的砂锅正冒着热气。 见我醒来,一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冲我一笑:“终于醒来了?”说着端着一碗稀饭一瘸一拐地走到我的床头:“先喝点稀饭润润肠子,看你一定饿坏了。 ”饥肠辘辘的我也不多想什么,端起碗稀里哗啦喝了三大碗,才算有了点活气。 “谢谢你!”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,想到这几天的遭遇,忍不住痛哭失声。 断断续续听完我的原委,小伙子默默地望着我,叹了一口气:“那你打算怎么办呢?”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“其实,我们不该为一次错误放弃未走完的路。 与其在歧路上越滑越远,不如返回重新开始。 ”小伙子语气很沉重,我则听出几分惊奇:“我们?难道你也有过我现在这样的经历?”小伙子皱着眉点了一下头。
“我那荒.唐而惨重的错误和你很相似。 而且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我的一条腿残了,是和别人打架时伤的。 ”我才想起,他是一个跛子。 “那次斗殴的结果的是,家里被前来报复的人捣了个稀巴烂,母亲气得跳了河。 是我害了母亲。 父亲拿了把刀说要砍死我这个逆子,我就跑了,再也没回去。 父母把我养这么大,不但没有得到我的报答,反而受尽了磨难和伤痛,我有时觉得我真是个十恶不赫的罪犯。 ”他说着说着将双手插进浓密的头发里,使劲地揪扯着,喉咙里挤出嗷嗷的哭声。 我不得不惊奇世事的巧合,一股同病相怜的冲动让我紧紧地搂住了他。
从此,我跟着他一起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干上了贩菜的行当。 我们早上四点就起床蹬着三轮车到郊区,从菜农手里进来一车蔬菜,然后拉到菜市场销售。 我们舍得花力气,菜价比别人定的低,一天下来薄利多销竟能赚得100多元钱,尽管很累,可毕竟有吃有住还能存下一笔积蓄,我很庆幸也很知足。 到了月底,他便将纯收入盘点平分,我坚持不要那么多,却抵挡不住他的强硬:“过去的事都过去了,我们现在是萍水相逢的朋友,能够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,就说明我们找回了自己。 我们并不是不可救药。 ”我就不再推辞。 除掉房租水电费,我们各自赚了800元钱。 他只从一沓钱票里抽出一张百元币,就将钱全部汇到了家里。 “我已三年没回家了,除了给家里汇款,我什么也没让家里知道。 ”他说这话时有点丧魂落魄,黯然神伤。 我也不由想到了父亲。 真不知他们急成了什么样了。 那一晚我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。
我想到了那梦魇般的生活。 人想到了渺茫而又无法逃避的前程。 我想到了父母忍受的耻辱。 难道真的一失足就得悔恨到坟墓吗?难道美好的青春就这样在市井的蝇营狗苟中得过且过吗?我在痛苦中反省自己,我在懊悔中诘问自己。 两个月后,我谢绝了他的挽留,毅然选择了回家重新开始。
刚好家乡在进行征兵体检。 我毫不犹豫地加入应征的行列。 感谢上苍,在历经失落和磨难之后,让我获得了一次涅盘的机会。 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。 如果说一身落时的衣着不可思议的让我迷失了自己,那么一身绿军服则让我奇迹般地获得了新生。 春天离我那样遥远,但我已脚步坚定地上路。
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,站岗放哨,摸爬滚打。 火热的军营生活一点一点融炼着我,敲打着我。 走过青春迷失的幽长隧道,我对黑暗之后的光明更懂得去珍惜和热爱。 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我利用空余时间悄悄捡起久违的高中课本。 第三年,我顺利考上了军校。
如今,军校毕业一年的我,已是一名年轻的共和国军官。 当我威武地走到队列前头的时候,又有谁知道我曾是一名被时光抛弃过的少年呢?站在阳光明媚的军营,我常想,堕落也许只是一瞬间的差错,而崛起则需要一段漫长的挣扎。 只有超越无法回避的过去,你才能获得生机勃勃的春天。 正视那些因为无知而留在履历上的斑点,正视划过心灵天空的阴影,让那段不光彩的灰色经历,成为一根插进神经的芒刺,成为知耻而后勇的不竭动力,这远比忘记它,或逃避它要好得多,因为忘记过去,就意味着否定现在,背叛将来。 作者:阿绍